|
牵牛花开 文/徐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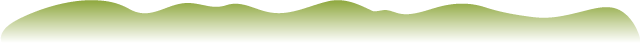
一
早秋清晨的阳光温柔地将露水擦拭得晶莹透亮,院墙里牵牛花细细的藤蔓抓着墙体突起的地方拼命往上爬,大门外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拼命地抓住最后的机会生长。这片肥沃的土地,夏秋季节被茂密的玉米覆盖,挡住了对于远方的眺望与遐想。冬季的皑皑白雪为他披上温暖的外衣,也阻隔了我们和土地的亲吻拥抱。唯有春季,嫩绿色的小草赋予大地生机和希望,那是我们童年的天堂。傍晚,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的白色气体与落日余晖交映在一起,奶奶做好的饭菜飘出的香气是召唤我回家的最大动力。
小时候的记忆里,天是长方形的。爷爷家有一架毛驴车,夏天的时候,爷爷就焊了铁架子支撑在四周,然后用帘布整个罩起来,毛驴走起来的时候,整架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帐篷,我特别喜欢躺在里边,把篷布掀开,让夏日的骄阳直射在脸上,闭起双眼,感受毛驴车轻微的颠簸,摇曳着童年天真烂漫的幻想。每次从枝繁叶茂的柳树下经过时,总是既担心又期待地睁开眼睛,看看是否会有油绿油绿的毛毛虫被柳树枝丫甩进帐篷里,艰难且不情愿地拖动自己肥胖的身体。那时的农村几乎是没有汽车的,一路上听到的是家禽的叫声和风穿梭在树林间的沙沙声,还有闲来无事的老人坐在柳树下拉动的二胡声,想着就这样悠闲地走下去,没有尽头该多好。然而上天用一次次打击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任何美好会是永恒。
毛驴病死了,并不是老死,没有任何征兆,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夏日清晨,悄无声息地离去了。爷爷找了几个人,把毛驴埋到了院墙外那片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任劳任怨春秋数载,不用过多言语去粉饰悲伤,这头毛驴对那时候的农村家庭来说有多重要,无需置疑。像一个亲密的伙伴安静地离去,有不舍但终会习惯,有悲伤也终会随时间散去。生老病死,优胜劣汰,任何事物都并非不可替代。
爷爷没有再买毛驴,一方面是因为没有钱,另一方面,毛驴其实是可有可无了,出行代步有自行车更快捷方便一点。毛驴车被冷落在墙角,唯有牵牛花紧紧缠绕,诉说着奔波的过往。颠簸的记忆渐渐模糊,只是每当我看到墙边停放的毛驴车和那已经被风吹的破破烂烂的篷布,还是会想起白云飘荡的四角天空。
二
奶奶养了一只大黑狗。大黑狗特别有灵性,每次我走到大门外,它都能听出来是谁,叫声明显温柔很多。进去之后它就立刻扑过来,蹭来蹭去,它站起来几乎和那时的我一样高。平时奶奶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它也摇摇晃晃地跟在后边。夏日傍晚,奶奶坐在柳树下的石墩上给我讲故事,它也静静地趴在石墩旁,眼睛半睁半闭,惬意地摇晃着尾巴。
晚霞会散去,余晖会消失,时光不会停滞。
2003年10月的某一天,家里的电话急匆匆响起,三叔告诉了我们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奶奶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已时日不多。那一年我刚上初一,第一次经历要面对至亲的人即将离去,第一次感受到面对死亡如此无能为力。
终于到了寒假,我迫不及待地去看望奶奶。这么多年第一次,大黑狗听到我的脚步声没有站起来,我走到它身边摸了摸它的头,它看了我一眼又缓慢地闭上了眼睛。
我走进屋里,看到奶奶坐在炕沿上,明显消瘦了很多,一声接一声地咳嗽,心如刀绞。我装作和以前一样,开心地扑过去抱住奶奶,给她讲我上学遇到的有趣事,骄傲地告诉她我又考了第一名。我紧紧拉着奶奶温热的手,我以为我不放开她就永远不会走。
初二那天早上,正好是大集,我看奶奶气色不错,咳嗽也有所减轻,就和爷爷一起带着奶奶去赶集了。回来的时候,大黑狗不见了,狗窝旁有一摊血,邻居老奶奶告诉我们,她在屋里听到了猎枪声,出来看到两个人把大黑狗抬上车跑了。我明显感觉奶奶的身体颤抖了一下。我到外屋给奶奶倒热水,透过窗户看到奶奶在低头抹眼泪。第二天早上,奶奶依旧把大黑狗的饭盆填满,每天如此,一直到她卧床不起。
农历十一月底,奶奶病情恶化了,家人日夜陪伴在她身边,咳嗽越来越厉害,进食越来越困难,她已经虚弱到嗓子里的痰都无法咳出来了。我多么希望奶奶能一直都在,哪怕只有一口气也好,但我那个时候只希望奶奶能安详一点走,不要受这么多罪了,没有什么比看着至亲的人在死亡边缘挣扎自己却无能为力更煎熬了。 腊月十八是奶奶的生日,她在人世间最后一个生日,儿女绕膝,子孙满堂。十九日早上,奶奶让爸爸把她扶起来,她透过窗户看向南方,目光澄净淡然,安静地结束了七十一年的生命旅程。
三
奶奶离开那一年,我13岁,第一次知道生老病死,要顺从天意。
爷爷离开的时候,我27岁,我开始明白,生命是一次单线旅程,且行且珍惜。
今年夏天,我回到老院子里走一走,牵牛花开了,只是不再成片,院子里早已刷上了水泥,几支牵牛花零星地挤在地面与院墙之间的缝隙里,艰难却顽强地生长。
小时候,总是喜欢坐在挂满星星的夜空下,细数未来,哼着悠扬孤单的摇篮曲,脑中满是对未来的无尽遐思,盼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大后,慢慢开始喜欢在夜深人静回忆往昔,将逝去不再的相聚寄予来生。现在终于开始明白,来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是一剂将自己遗憾与悔恨的痛尽可能减轻的苦汤药,我们明知没有疗效,却甘愿一次又一次的服下,苦到让自己暂时忽略伤疤和疼痛,然而我们都忘了,遗憾和悔恨,是绝症。治不好的。
(责任编辑:刘月新 制作:胡君涛 图据网络) 徐帅,笔名易寒,90后,公务员,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人。库伦旗朗诵学会主席,库伦旗美术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火红的安代》杂志副主编。
投稿须知请勿一稿多投,已在其他公众号发过的,请勿投。来稿请附上120字以内的简介和照片。征文投稿第三天可查看邮箱或群里每日预告;长篇稿件一月之内未发表的,可自行处理。
文章校对后只修改一次,请定稿后再投稿。投修改稿时请一定注明“修改稿”。 长篇稿件要求1500字以上。 此为《在场》杂志选稿平台,在场团队有权对文章进行修改和推广,如不同意,请在稿件中注明。 关于稿费普通作者返一半,贫困作者扣除腾讯运营费后全返。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库伦元火网
( 蒙ICP备13001995号-1 )|网站地图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库伦元火网
( 蒙ICP备13001995号-1 )|网站地图 蒙公网安备 15052402000112号
蒙公网安备 15052402000112号 